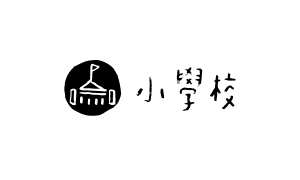拿出書架上的歐洲藝術史、翻開文藝復興Renaissance那一章,許多的撰寫者會從前身拜占庭美學Byzantium或前輩喬托Giotto di Bondone(1267-1337)的聖母像開場。然而無論如何進入那個時空,都會自然地標記出關鍵的發源聖地:佛羅倫斯Florence。接著讀者們會反覆讀到「麥迪奇家族House of Medici」中好幾位強而有力的資源輸出者。那麼為什麼麥迪奇是文藝復興時代最廣為人知的姓氏呢?而今日的我們能夠從哪些有趣的角度,去觀看這個家族與人文主義Humanism 復甦之間的關係呢?

《百花聖母大教堂》外觀。圖/wikipedia
麥迪奇家族就如同文藝復興時代的一個龐大背景,反覆在不同的藝術家傳記中入鏡。他們贊助過無數文化建設,支持了大半教廷財務,在西方乃至人類文明的拼圖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六百年多後的當代,如果以社會發展的角度審視麥迪奇家族,或許能從中更加理解當時「藝術家們的養成與處境」。
從瘟疫橫行到人本精神再現,14世紀初的歐洲大陸正處於毀滅與重生之間。當時的義大利半島,對內對外都處於烽火之中,人們的內心「探詢生命意義」的需求越來越明確。或者說,群眾開始需要比文字(聖經)更具感染力的視覺(繪畫 / 雕塑)做為靈魂的寄託。然而想要重拾人性的光明,單憑藝術家、思想家的覺醒是遠遠不夠的,真金白銀的資源往往才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關鍵。但在沒有前例可循的時代裡,願意耗費資源資助未知的嘗試更是相當不容易。卻也就在這個時刻,「麥迪奇集團」適時地成為了藝術家的夥伴,以文化建設滿足了當時群眾的精神需求。

《百花聖母大教堂》內部穹頂,多位藝術家合作的「最後的審判」主題壁畫。圖/wikipedia
麥迪奇家族起源於法國,13世紀末移居義大利後蓬勃發展。這個成員眾多的姓氏(至今可追溯的分支仍有近30支),前後曾經出生兩位法國女王、四位教皇、多位佛羅倫斯共和國主教,並且取得了佛羅倫斯公爵的世襲資格及紡織品、染料、香料的貿易優先權。
穩固的政教關係,成為了麥迪奇家族發展貿易與金融業的基礎。而經商獲利的金幣銀幣,又繼續支援著家族相關的政治人物、宗教人物獲得權力。最終形成了一種類似今日「政治獻金與法案訂立」的循環關係。若以當代的社會結構來類比,麥迪奇家族隱約扮演了是某種「立基於宗教的政經集團」角色。

《百花聖母大教堂》正門上方,多位藝術家馬賽克拼貼壁畫。圖/wikipedia
麥迪奇家族遷居義大利半島後,第一代被記載的人物是薩爾維斯特羅salvestro de medici(1311-1388),他曾經擔任過司法職務-正義旗手。卻也曾因為支持的派系垮台,被逐出佛羅倫斯。他的兒子,第二代的喬凡尼Giovanni di Bicci de' Medici(1360-1429)從羊毛紡織業發跡、創立了麥迪奇銀行,並努力在義大利半島廣設分行,為接下來二百年的家族輝煌奠定下了實質的基礎。
雖然喬凡尼對於親身參與政治並不熱衷,卻有著敏銳的投資眼光。多次在宗教爭權的當中正確下注,讓接下來的多位教宗都委託麥迪奇銀行管理財產。在那個贖罪券熱銷的背景下,教宗的財務顧問無疑是一個掌握龐大利益的職務。與教廷的良好關係,也支援著喬凡尼其他事業的能夠很順利地發展。

多納泰羅,《大衛像》,青銅,158 cm,約1440。圖/wikipedia
藝術贊助往往是從熟識的朋友開始的,財務上的餘裕讓喬凡尼陸續資助了好幾位藝術家好友創作。其中包括了多納泰羅Donatello(1386-1466)的雕塑、布魯內萊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1377-1446)的建築等等。例如象徵著城邦精神的《百花聖母大教堂》和《聖勞倫斯大教堂》都是非常成功的作品。也自喬凡尼開始,麥迪奇家族開啟了資助藝文活動的優良傳統。
當麥迪奇家族傳承到了第三代科西莫Cosimo di Giovanni de' Medici(1389-1464)時,已經坐擁了富可敵國的家業。但年輕時科西莫也和祖父類似,也曾因為當地政爭而被佛羅倫斯流放。有趣的是,憑藉遍佈四處的家族產業,科西莫在羅馬、威尼斯等地結交了更多的好朋友。這段時間的經歷,也在未來支持著科西莫將金融版圖擴散至全歐洲,甚至跨海在倫敦設置了分行。

《麥迪奇宮》外觀。圖/wikipedia
在科西莫離鄉期間,如果發現某個城鎮缺少某項建設,就慷慨地直接撥款資助。其中科西莫最熱衷贊助的是教育事業,例如就曾經委託建築師米開羅佐Michelozzo(1396-1472),送給了威尼斯一座「漂亮的」《修道士圖書館》。這一段流放生活科西莫過得很瀟灑,簡直就是一場布施之旅。直到佛羅倫斯的議會受不了大量資源外流,才只好懇請科西莫回到故鄉。

《麥迪奇宮》內部。圖/wikipedia
很難說科西莫賺錢或花錢的手法哪個比較高明。但是他掌握家族時,扎扎實實地延續著父親的藝文喜好,邀請好友米開羅佐和畫家貝諾佐Benozzo Gozzoli(1420-1497)打造了樸素而宏偉的《麥迪奇宮》。由父親開始的《佛羅倫斯大聖堂》也在科西莫手上順利完工。這時期的科西莫也繼續資助了家族好友多納泰羅,完成了著名的青銅像《大衛》。
以繪畫而言,科西莫的支持讓安傑利科修士Fra Angelico(1395-1455)等等藝術家們能夠專注作畫。此時的畫家訓練,雖然依舊在宗教神話的範疇,但已經不再只是出版品的的一環。推崇「全才」的思維成形,使得建築、雕塑甚至幾何數學的訓練成為了藝術家們共同的養成背景。這些養成訓練,最直接影響就是在平面藝術中出現了明暗感和立體感。這群藝術家們漸漸發展出與拜占庭 / 圖式美學不同、體現著透視觀的繪畫(更貼近現實世界)。雖然這樣的繪畫形式在當時的定位接近於「實驗」,但已經開始將繪畫與插圖的概念作出區分。由此開始,視覺圖像不再只是聖經或史詩的輔助、不再依附於文人體制,而是漸漸成為了一個獨立的學科。

安傑利科修士,《天使報喜》,蛋彩壁畫,230 x 312 cm,1438-1450。圖/wikipedia
在戲劇化的一生中,科西莫熱情贊助了無數的城鎮辦理教育。例如在1444年,科西莫出資建立了佛羅倫斯第一座公共 / 免費圖書館。更難得的是,科西莫聘請了大量的「尋書者」遠赴埃及和敘利亞等地,對於古典的哲學思想進行考究、翻譯和抄寫。這是一個很關鍵的取經,很大程度地引導了後世哲學的發展方向。熱衷於柏拉圖學派Platonism 的科西莫,委託了神父費奇諾Marsilio Ficino(1433-1499)翻譯了史上第一套柏拉圖全集的拉丁文版本。他也在1462年成立了教育機構「柏拉圖學園」,為生命本質的辯證重新開啟了系統。一系列的工作,為「與神學同等重要的哲學」奠定了相當關鍵的基礎。
諸多文化建設的出資,讓科西莫在故鄉獲得了極高的聲望。雖然當時的藝術表現依舊有題材上的慣性,但也開始有了越來越自由、生動的發揮空間。這樣的氣氛,成為了佛羅倫斯超越其他城邦的重要因素。這些生命力充沛的藝文產物,連結了神性與人性。在識字率不高的中世紀,為市民提供了活力與認同感。
畢竟藝術與人文對於尋求寄託的市民而言,常是最好的撫慰。而這對於統治階層而言,則是能夠直觀團結群眾的有力工具。若將時間軸再延伸來觀察,文藝復興時鼓勵突破的氛圍,首先使得宗教與政治的權力回歸到了「人」的手中。接著這樣自由探索的精神,漸漸演化為西方世界的慣性。如今看來,這樣的傳統也是歐美各國取得全球主導的原由之一。

波堤切利,《春》,木板蛋彩,203 x 314 cm,約1482。圖/wikipedia
對比父祖輩的成就,麥迪奇家族第四代的皮耶羅Piero di Cosimo de' Medici(1416-1469)因為身體狀況較差,大抵上屬於守成的定位。但傳承到了第五代的羅倫佐Lorenzo de medici(1449-1492)時,他承繼了祖父對於藝文的使命感,將更大量的資源挹注進入藝文建設。羅倫佐善用了天時地利,其治理下的佛羅倫斯一時之間人才輩出,城邦的聲望也在歐洲各地脫穎而出。
許多的藝術史巨擎:波堤切利Sandro Botticelli(1445-1510)、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1475-1564)、拉斐爾Raffaello(1483-1520)等等,在青年時期都接受過麥迪奇家族的資助。這讓大師們在養成階段,就有機會接受完整的人文學科 / 工藝的訓練。而提供了大量教育資源的羅倫佐,就像是一位四處開設「平價私校」的校長。長期穩定的教育支持,則讓他被後世稱為「奢華者」或「慷慨者」。

米開朗基羅,《創世紀》,蛋彩壁畫,230.1 x 480.1 cm,約1511。圖/wikipedia
上百位受羅倫佐資助的藝術家中,最為人樂道的,就是米開朗基羅曾經以類似養子的身份,與羅倫佐的子姪們共同生活、學習。期間與優秀的同儕在同一張餐桌上,討論如何詮釋聖經成為了日常。即使羅倫佐過世之後,米開朗基羅也與麥迪奇家族的成員們交好。麥迪奇家族出身的教皇李奧十世和克萊門七世,都曾委託米開朗基羅工作,例如西斯汀教堂的壁畫《創世紀》和巨大的《摩西像》都是著名案例。而另一位偉大藝術家達文西,則是在手稿中寫下了一斷耐人尋味的文字:「一部分的麥迪奇家族造就了我,而另一部分的他們毀滅了我。」可見麥迪奇家族對於當時的藝術家們,具有相當巨大的影響力。
此時的佛羅倫斯已經是歐洲數一數二的商業城邦,相對富裕的社會成為了其他地區所嚮往的指標。若將「羅倫佐時代」視作文藝復興的第一個高峰,期間作品所象徵的已經不再單純是人本思維的重生,而是一種集體復興的成就。做為文藝復興的發源地,佛羅倫斯自然地成為了所謂的「進步代名詞」。

達文西,《聖母聖子與聖安妮》,木板油畫,168 x 130 cm,約1503。圖/wikipedia
或許贊助者和創作者最初在面對藝術時,並不具有過多的目的性。但在羅倫佐接管家族後,開始將長期累積的文化資本,做為城邦價值的象徵物對外輸出。於是在多方的有意識的推動下,「人文精神」成為了各城邦趨之若鶩的時尚。曾接受麥迪奇家族贊助的藝術家,也像是獲得了鍍金認證一般廣受歡迎。在麥迪奇家族的背書之下,不同類型的藝術家們都能在各地獲得很好的工作邀約。
具有新意的藝術品、藝術風格在訊息傳遞緩慢的中世紀,很容易成為最直接的價值宣傳。試想當時歐洲的某個地區,尚處在黑死病籠罩末期,有一位藝術家在教堂壁畫中帶來了充滿希望的(佛羅倫斯來的)藝術樣貌。會在所謂的落後者心中,很直覺地造成對領先者的嚮往。而這些現象,也使得麥迪奇等等大家族取得了更大的社會話語權,進而更加樂於資助藝術文化的發展。當崇拜形成了模仿,大量模仿形成趨勢,文藝復興的風潮就開始由南向北地蔓延了開來。

拉斐爾,《雅典學院》,壁畫,500 x 770 cm,約1511。圖/wikipedia
可惜的是,在羅倫佐掌權的後期,麥迪奇銀行開始因為分行呆帳和公款挪用等等問題開始衰退。1492年羅倫佐過世,同年哥倫布在美洲上岸,世界的貿易版圖開始改變。1494年法蘭西攻打義大利,麥迪奇家族投降,迫使麥迪奇銀行的最後七家分行關閉。羅倫佐的長子,家族第六代的繼承者皮耶羅Piero di Lorenzo de' Medici (1472-1503)被稱為「不幸的皮耶羅」。他雖然繼承了資源,但並沒有繼承到家族前輩的品格。揮霍無度的生活,終於導致麥迪奇家族在佛羅倫斯的統治被推翻。

米開朗基羅,《摩西》,大理石,235 x 210 cm,1513-1515。圖/wikipedia
雖然家族中第七代的喬凡尼 Giovanni di Lorenzo de' Medici / 李奧十世Pope Leo X(1475-1521)和朱利奧Giulio de' Medici / 克萊門七世Pope Clement VII(1478-1534)曾分別擔任教皇,試圖以宗教的力量恢復家族地位。但在漸漸普及的復興氛圍下,中產階級日漸崛起。這時候人本思維也在歐洲已經成為主流,不同背景的藝文作者們都開始由此出發創作。商業資源的轉移,象徵著藝文資助者的結構改變,更讓麥迪奇家族失去了優勢。雖然龐大的家族成員們依舊維持著熱愛藝文的傳統,但卻再也沒有在商業或政治上取回全盛時期的領導地位。
如今麥迪奇世代累積的收藏品,大多被烏菲茲美術館Galleria degli Uffizi及帕拉提納美術館Galleria Palatina收藏(這兩座美術館的建築也是由麥迪奇家族出資興建),成為了向公眾開放的人類共同財產。這一切歸功於麥迪奇後代中一位重要的傳奇人物安娜Anna Maria Luisa de'Medici(1667-1743)。她留下了:「將麥迪奇家族所有收藏品都留在佛羅倫斯,向公眾開放展出。」的遺囑。不僅完整保存了家族的輝煌紀錄,也讓後世有機會看見文藝復興起點的完整樣貌。

米開朗基羅,《麥迪奇的聖母》,大理石,226 cm,1521-1534。圖/wikipedia
無論古今,當巨大的權力缺乏制衡就必然會出現政爭或革命。麥迪奇家族的興衰,在諸侯林立的城邦時代並非特例。即使麥迪奇集團是義大利數一數二的貴族,但以全歐洲而言,依舊不可能完全掌握情勢。這個家族對外曾經歷過多次的打壓,對內在後期也經常面臨著挑戰。例如同時代的巴迪家族House of Bard、阿博提家族House of Alberti等等,均同樣立足於佛羅倫斯,也經營著巨大的事業,各家族之間也常有聯姻、互相牽制。

(由左至右)麥迪奇家族支持文藝復興的代表性人物:第二代的喬凡尼Giovanni di Bicci de' Medici、第三代科西莫Cosimo di Giovanni de' Medici 和第五代的羅倫佐Lorenzo de medici。圖/wikipedia
若說麥迪奇家族以一己之力,支撐了文藝復興的起點,或許並不為過。從14世紀初開始大約兩百年的時間裡,麥迪奇家族與佛羅倫斯的興衰緊密相關。如果說藝術家們是巨樹,古文明是雨水,時代氛圍是陽光,那麼麥迪奇家族家族就是土壤。雖然其家族的輝煌並未延續,但依舊無損其各個階段的成就。
回望麥迪奇家族發展的前期,非常明確地要求家族成員要「像個佛羅倫斯人」一樣生活。從飲食穿著到遵守法律,都期望成員與市民生活在同一個立場(相對簡樸)。巨額的財務開銷也都只會出現於宗教、藝文、城市建設和軍事防禦。這樣「奉獻者」的形象,使得麥迪奇家族在故鄉取得了不可動搖的支持。但當後繼者偏離了奉獻精神,失去支持也就成為了必然。

《佛羅倫斯大聖堂》外觀。圖/wikipedia
無論是從那些被支持的藝術家、藝術品來看,或者從人文主義的傳播而言,麥迪奇家族的重要性都很難被量化。我們甚至可以隱約從麥迪奇家族對於藝術人文的「成果發表」中,觀察到「當權者如何運作話語權和認知體系」。某些類似宣導式的文化輸出,如今看來也能夠與當代文化的版圖消長(例如日本的動漫產業或美國的電影產業)相互對照。「從宗教出發、以人性為本、推崇創新與挑戰的精神」至今依然是西方世界的主流思維。文藝復興之後出現的種種藝術流派、資本主義甚至工業革命,都在某種程度上延續了這樣的價值觀。
好的創作者必然會與時代對話,或許由於自然、經濟、政治、宗教或者什麼樣隱性的因素,種種感知都會成為作品的一部分。想要從單一的藝術家或風格,來推論時空環境其實並不容易。但若是從一個大的時空背景來觀看藝術家們,我們將能夠覺察到許多的偶然與必然。換個方式去審視熟悉的事物,總是能得到有趣的收穫。或許再過幾個世紀,後人也會察覺到今日的藝術有那些值得討論的地方。為了到時候不要被形容成黑暗的21世紀,各位藝文工作者們就請好好繼續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