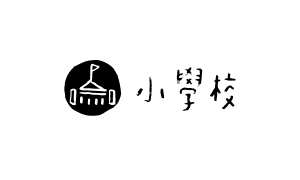我們的後面是什麼?
在某次與一位藝術評論前輩聊天時,談到了臺灣當代創作面對的議題討論之空缺狀態。展覽跟展覽之間,缺乏著策展問題意識上的對話與帶動,一個具有特定命題的策展,鮮少會回顧另一些可能與之有所對話的過往展覽。
同樣地,創作缺乏屬於自己的論述脈絡的持續建構,又或是對當代的創作者來說,不再是首要的問題。相對於建構論述,如今的環境使許多創作者需花費更多時間成本在爭取曝光,願意與臺灣藝術史中的藝術創作進行對話的當代藝術家少之又少。
跟臺灣藝術史相比,歐美藝術史與我們要親密地多。這或許是藝評人陳韋鑑在評論此展時說的「主體的空缺」(註1)。這種主體語境的空缺,讓我們在想到關於藝術的藝術時,第一個浮現在腦中的總是歐美藝術史的經典案例。如果那個藝術是關於藝術的,那麼很多時候它是與過往的歐美藝術史典範進行單方面的神交。
這是《穿越人煙罕至的小徑》作為「跨世代對話」的第一層意義與問題意識。林壽宇曾在1985年以〈我們的前面是什麼?〉為鋼雕作品命名,進一步質問臺灣藝術環境還有什麼可能之處,如今也許我們需要翻過來再問一次:我們的後面是什麼?

《穿越人煙罕至的小徑》二樓展場中,策展團隊把和三位藝術家有關的各種歷史條目索引輸出成壁紙。這些條目像是藝術流動之河中的一顆顆鵝卵石,或是歷史之毯中一條條經緯織線。圖/非池中藝術網攝

林明弘作品〈2號構圖〉掛在裝置作品〈展位〉的支架上,《穿越人煙罕至的小徑》二樓展場。圖/北師美術館提供。張國耀攝影
潘洛斯三角
儘管顏水龍的木椅與林壽宇的作品明顯分屬不同脈絡,但這個展示的支撐結構賦予他們一個可供深入探究的共同基礎......顏水龍的〈麻繩椅面木椅〉在製作當時可能不被認為是藝術,但在藝術定義儼然擴張的今日,我們鑑賞他的方式也更加多元了。
——《穿越人煙罕至的小徑》導覽文字
藝術的定義又是如何在今日擴張的?在臺灣的擴張過程,跟以美國為核心的20世紀藝術史中的擴張過程又是否有何種對話空間?顏水龍與林壽宇在美學觀念與家庭背景之間的極端,在林明弘創作架構下的展場支架與結構,成為了一個關於現代主義藝術、實在主義(literalism)在物性中追求的一種劇場性和在場,以及美術館展示方法的提問。
如同《穿》展的導覽手冊中提到的,「你會意識到自己總是在一位藝術家作品的環境中,凝視著另外一位藝術家的作品。為了進入下一個畫面,你不得不繞過〈展位〉,這些遮蔽、迂迴、借景,是由你身處其中的移動所展開的。」 展覽的規劃使我們不單純是在觀看展覽中的每一件作品,每次觀看的前景、中景與遠景,都意圖使你意識到自己置身在這三人同台飆戲的(一種在藝術與藝術之間的)劇場性觀看當中。
走上二樓,迎面而來的是林明弘停在右手邊的九輛精美的永久牌腳踏車,背景是由搶眼的巨型印花紋構築而成的牆面,這個源自於日常生活中轉化而來的包裝,成為以暖黃光照明著的顏水龍素雅竹編傢俱的背景。左側鮮紅的林壽宇裝置很難不引起你的注意,琳瑯滿目的大型裝置分別在我眼前不同角度揮手時,我的選擇性困難讓我隨意地選擇了其中一條看展的小徑。
走上三樓,林明弘的〈日間床〉正等待我們的觀看,放在這個作品之上的,是顏水龍的檯燈,暖黃光與它身後反射冷咧白光的林壽宇作品〈千山我獨行〉,讓我意識到展覽團隊對於光的細膩掌握。在二樓主展場中的光主要以暖黃光為主,使顏水龍家具更瀰漫著一種生活的溫度。三樓後半部工業感的冷白光,則將我們拉回到一塵不染的白色殿堂,現代化工業式的、美術館式的冷與白。

《穿越人煙罕至的小徑》二樓展場。圖/北師美術館提供。張國耀攝影

《穿越人煙罕至的小徑》二樓展場。圖/北師美術館提供。張國耀攝影

這個展覽使藝術價值之間的對話之所以有效接著,而不只是落入一種單純的作品聯展之關鍵,在於策展團隊有意識地透過藝術史方法與空間調度等面向,將藝術、物性(一個東西作為非藝術的條件)與生活這三個形塑戰後世界主流視覺藝術論述的支點,以及在《穿》展中的這三位藝術家的藝術思路,形成了一種如潘洛斯三角(Penrose triangle)般、看似以不可能的迴路纏繞方式進行的對話思路。
策展人之一的郭昭蘭,在其論述中有意將藝術家的作品進一步理論化,讓形式主義—這個在後結構主義批判之後成為髒字的美學方法,在臺灣有全案上訴重新審視的可能。這次,我們可不能只是再次於這些藝術家的作品中,尋找他們如何效仿著各自所信奉的藝術形式之表象痕跡。這個展覽所有作品內外的物性,那些連煙火式藝博會都極力隱藏其臨時性的展牆支架、簍空的台座、IKEA的櫃子、顏水龍設計的太陽餅包裝盒等,都一再地以提醒我們,重新留意形式主義美學在藝術,物性,以及裝飾性紋樣之間的纏繞(註1)。
在這裏,在關係美學中用來與共活性(conviviality)價值相結合的展示本身,將反身地成為上述倒置關係中的認識對象 ,催生一種以本地藝術脈絡為對象的跨歷史認識途徑,使展覽中的人、物、與形式,一併在此因展示活動而共謀衍生特定意義;而是否,這可能將不只是對於本地的藝術史方法提出相對於世界藝術史的修正動能,而是更積極觸及區域藝術實踐在面對世界藝術時的主動性?
——郭昭蘭,〈活性與惰性的互換〉
物性的光譜
這個展覽讓我們在錯綜而看似路線彈性的展場規劃中,慢慢品味在百年來的「非藝術」如何介入藝術的發展過程,而作為臺灣三個世代的藝術家,又是如何在這個量子糾纏的過程中帶出新的觀看方法。
物性與藝術之間的當代光譜如今是如此多元,已非格林伯格 (Clement Greenberg) 、唐納德・賈德 (Donald Judd) 與邁克爾・弗雷德(Michael Fried)論戰的低限主義、特殊物件 (object sepecific) 抑或是實在主義的時空背景所能比擬(註3)。在《穿》展中,所謂的物性光譜,至少有著油彩繪畫—後繪畫性抽象—現成物裝置—空間裝置—工業設計傢俱—低限的平面設計—規格化的展牆與支架,作為光譜中的幾種色階。管裝顏料作為工業化侵入繪畫的一種表現,使至今大多數的繪畫,幾乎都是自現成物中轉化的創作(註4)。這使繪畫創作在一些低限主義論者的眼中,成為了一個在前衛意義上近乎山窮水盡的藝術。這與林壽宇在1984年「封筆」、並著眼於以現成物表現的後繪畫性抽象有著共鳴(註5)。
林明弘曾多次談及他在伊通公園的吧台手工作經驗,這個經驗使他對於展覽與日常生活之間邊界的認識,有著貼近關係美學式的切入點。也正是這層理解,讓藝術家在創作裝置時對藝術與非藝術的邊界,擴張至如林明弘放置在顏水龍〈竹製客廳桌椅(桌)〉(1991)的(法國品牌邀請林明弘設計的)瓷盤,都在這個展場中成為一種翻轉特殊物件的、一種作為藝術的物的展呈與放置,藉此回應到林壽宇在絕筆之後的、孤高的低限主義式的觀看。

《穿越人煙罕至的小徑》二樓展場,左側作品為林壽宇的〈封筆-1〉(1984),它被掛在林明宏的裝置〈展位〉中。圖/北師美術館提供。張國耀攝影

《穿越人煙罕至的小徑》三樓展場,顏水龍、林壽宇和林明弘的手稿、影像紀錄、包裝設計和裝置作品錯落在展場之中。圖/北師美術館提供。張國耀攝影

林壽宇作品〈無所在無所不在〉(2010)於《穿越人煙罕至的小徑》三樓展場。圖/北師美術館提供。張國耀攝影
如今,我們感受到的「實在」是什麼?
相對於林壽宇孤傲高冷的低限與實在主義思維,先是作為畫家、而後成為臺灣工藝復興火車頭的顏水龍,其在藝術與物性的認識過程中,美學之手的介入,讓人想到承襲自包浩斯和黑山學院中的手工藝精神。顏氏所創作和設計的物,在裝飾性、實用性的美感中,在如今透過藝術、物性與裝飾性在展場中的纏繞裡,反而成為對實在主義最有力的反問之一。
它作為《穿》展的第二層意義,是以此作為回應戰後現代主義藝術與低限藝術美學的理論化或知識化的策略。在當代的生活與蜿蜒錯綜的展場中,觀看由IKEA傢俱組成的裝置還有擺放在桌上的包裝盒時,裝飾性如何擾動低限主義中的實在性?我們感受到的實在是什麼?單就一個展覽或是一篇文章,可能尚無法提出一個更肯定的回答,然而這個展覽透過林明弘的裝置,牽成林壽宇和顏水龍這兩個臺灣藝術世界的極端,成為了我們在思考形式的討論如何在當代復返的一條路徑。
在臺灣,藝術史與方法論的辯證之河,如同時而暴漲、時而乾涸的流域。的確,臺灣當代藝術更親近於西方典範而非自身的歷史,這是現階段的環境造成必然的斷裂性,也是臺灣藝術史至今的特質。但這並不表示我們不應該試著努力在這之中,在折枝之處尋路。相反的,這種看似雜草叢生的地方,正代表著無限可能的道路。這樣一來,或許我們在集結臺灣前輩藝術家作品的大展「不朽的青春」中,或許就更能發現那些可為當代參考的藝術美學價值,而不只是純粹以歷史價值,以一種蓋棺論定的觀看方式欣賞作品。

《穿越人煙罕至的小徑》二樓展場。圖/北師美術館提供。張國耀攝影

《穿越人煙罕至的小徑》一樓展場。圖/北師美術館提供。張國耀攝影
註 1:詳見陳韋鑑於台新獎網站上對於北師美術館「穿越人煙罕至的小徑」之評論。
註 2:在本篇文章完成之後,策展人郭昭蘭進一步回應此處更是「重新留意形式主義美學在藝術,物性,以及「裝飾性紋樣」所牽涉的區域與全球展示機制之間的纏繞」。
註 3:後來邁克爾・弗雷德在自己出版的書中,甚至也進一步向讀者修正、釐清了自己對藝術與物性的看法。在《藝術與物性:論文與評論集》的導論「我的藝術批評家生涯」的一個節選部分中,他在1990年代編輯該書時,對1967年《藝術與物性》一文的回顧性評述。詳見弗雷德,《藝術與物性:論文與評論集》,張曉劍、沈語冰譯,江蘇美術出版社,2013年。
註 4:詳見比利時學者德・迪弗(Thierry de Duve)於1986年的論文《現成物與顏料管》。
註 5:學者陳譽仁在2010年的文章〈減法的極限:林壽宇的回歸與台灣低限主義前史〉中,梳理了林壽宇的低限之於當時藝術家與其面對的臺灣藝術環境之間的關係。林壽宇在英國歷經從Lin Show Yu改名為Richard Lin、於皇家藝術學院擔任教職、並作為一位被視為「英國」藝術家的「中國」藝術家,返台之後面對到因階級而異的環境,是「使他不再能夠在創作上找到可以對話、競爭的對象。......藝術創作最怕處在沒有真誠批評、真誠讚賞的世界裡,而當時的臺灣正給予了林壽宇這樣的環境。」

《穿越人煙罕至的小徑》展覽外牆。圖/北師美術館提供。張國耀攝影